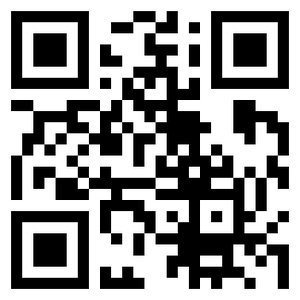成功的姚崇、宋璟因成功而遭到了抛弃,唐玄宗面对天下已治的局面,开始物色合乎心意的新人选专业配资网站,标准似乎是不要太冒尖也不要太无能。
1、副宰相的权势第一人选,首席宰相人选;玄宗决定让和姚崇一起下台的源乾曜复出担任。
第二人选,即副手人选,玄宗脑中早有了形象,却怎么也记不起姓名,苦思多日,依稀只记得是北方的封疆大吏。夜阑人静,他把值班的中书侍郎韦抗叫来询问,说是朔方节度使张齐邱,当即起草了任命诏书,待韦抗走后,他随手拿起大臣的奏章阅看,忽然,“张嘉贞”三字跃入眼帘,又忽召韦抗回来改写任命书。
侥幸,侥幸,张嘉贞的拜相真是侥幸之至。君主择相竟有着如此的随机性。张嘉贞给君主留下的好印象,不是才干,而是度量。
他先前担任北方部队将领时,曾被人弹劾奢侈挥霍及受贿,经御史台调查核实,发现是无中生有的诬告。玄宗下令追究弹劾者,不料受害者却豁达地说:“百官谏,庶人谤,由天子斟酌。若反坐此人,则将堵塞言路,天下事难以上达。望能赦免此人之罪,以开天下言路。”
展开剩余90%弹劾者未达到目的,张嘉贞却以此事受到了君主的注目。
“宰相肚里好撑船”,玄宗心里从此有了个候选人。
源乾曜是个好好先生,没有因成为中枢首席长官而拿出独挡一面的气概,仍表现得宽厚、仁和,很少发表独到的看法,凡事都以退让为上。
张嘉贞这个军旅出身的宰相,保持着军人的爽直,他思维敏捷,再大的事都能在片刻中作出决断,有着强烈的责任感,但性格暴躁,为人刚愎自用,和同僚们的关系相处得极为紧张。他对部下只信任苗延嗣、吕太一、崔训、员嘉静四人,形成一个小团伙,被人讽刺为“令公四俊,苗、吕、崔、员”。源乾曜和张嘉贞倒相安无事,然决谈不上关系融洽。源乾曜保持了过去当副手的作风,遇事都听凭当仁不让的张嘉贞裁决。
正职变成了副手,副手行使了正职,虽然无碍大局,但总让人们觉得有些异样。玄宗不会不感到这种异样,这种异样实际上是他刻意安排的结果。正副手的颠倒,巧妙地进一步抑制了相权,因为一个副手再包揽大权,毕竟有些不方便。
不易察觉的巧妙更为巧妙,玄宗的权术玩得炉火纯青。
张嘉贞提出对军役制进行改革。当时军队采用府兵制,部队平时为农,战时成军,21到60岁为服役期,几乎是终身制。旷日持久,军官把士兵视为家奴,任意扣克军饷,加派劳役,造成群心怨愤。张嘉贞缩短服役期,年龄定在25到50岁之间,并由百姓轮流参军。此计划和源乾曜联名上奏,得到了玄宗的批准。
源乾曜的贡献在于改变重京官轻外官的风气。时高官子弟以受荫方式多留为京官,出身低层的科举者却大量被派到边远地区。源乾曜主动将两个担任京官的儿子放为外官。他的以身作则,引起了积极的反响,不出多时,100多个高官子弟被他们的父亲送到了外地。
张嘉贞春风得意的时间不长,未出三年就败了,败在东山再起的大功臣张说手下。
他没有什么把柄抓在政敌手中,而是受到弟弟金吾将军张嘉佑贪赃事的连坐,被贬为幽州(今北京市等地)刺史。
2、张说的失算尽管梦寐以求,但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还能东山再起,接到再次拜相诏书的张说,心情之兴奋远远超过当年的谢安。
让张说复出,并不意味玄宗对功臣产生负疚感而作出补偿。
多年来张说不断活动以求出山,都被置若罔闻,现在作出这个任命,是玄宗对张说的个人才干再度发生了兴趣。张说是个勇者,河曲(今山西省芮城县西风陵渡一带)羌族因与政府军发生冲突,他仅带20轻骑冒险进入其境对酋长进行了解释和安抚,以和平方式解决了争端。他是个智者,在与太平公主对峙期间,以情理并茂的一席谈,使睿宗把监国权授与了李隆基。他还是文坛领袖,和苏颋(两人分别爵封燕国公和许国公)被誉为“燕许大手笔”。
有勇有谋,且有文才,张说是个难得的人物。
自让姚、宋告别政坛后,玄宗在施政战略上作了重大调整,明确皇权是主宰,相权是附庸,让一般之臣取代名臣,自己增多出面机会,如主持殿试,对县令训示惠民方针等。他的用意在于说明天下大治的局面是在他的英明领导下形成的,为了让昌盛的局面持之以恒,他需要听话的宰相来加以维持。然而实验的结果,却不尽人意。他看到源乾曜、张嘉贞无力负责这种局面,大量涌现的新问题及沉淀的老问题,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。
在此状况下,玄宗召回了张说,这是迫不得已的举动,希望他能让中枢出现生机。
由此张说与张嘉贞发生权力之争时,玄宗站在了前者的一边。
张说此次入相,欣喜之下充满着余悸,通过多年的君臣交往,他看透了玄宗,只是缺乏隐士的素质,为了荣华和权力,又踏进了地狱般的天堂。他曾半是牢骚半是攻击地对张嘉贞说:“宰相遇时而为,岂能长据不退!”
张说有些贪小,出于贪小他上了姚崇的当。姚崇死后,他前去吊唁,因受了姚府的厚礼,为死者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碑文。
事后觉得不对,前去索还,但石碑已经镌成。他懊恼无比却又打心底里佩服,说:“死去的姚崇犹能算计活着张说,到今方知我的才能远不及他!”
张说有才干,凭着才干要干大事,要做出成绩,要名满天下。
他聪明得很,也愚蠢得很,聪明在能抓住重大问题进行突破,愚蠢在不懂国情人情等潜伏牵制因素。
他成功了,成功之日再次跌进惨败的深渊。
张说任内做了三件大事:
经济方面取消职分田,受田的农民直接向政府交定额租,由此避免了官员的中间盘剥,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。设立公廨钱,作为百官俸禄。军事方面对军制进行大改革。以全家性命作担保,将日益腐败、失去战斗力的府兵裁军20万。另行募兵制,建立“彍骑”部队,作为军队的主要成分。政治方面为提高相权,加强办事效率,建立中书省、门下省这二个最高决策机构的联合办事处——“中书门下”,从而把权力全部抓到了自己的手里。事情确实做得有魄力,有起色,功在朝廷,功在社稷。然而在他得意的背后,却危机四伏,取消职分田,官员怨;裁汰军旅,军官怨;提高相权,皇帝怨。
这些怨尚是暗怨,远怨,因他重用文士,排斥吏才,对同行动辄翻脸叱骂,又招来近怨,明怨。
他身处险境,却不以为然,利令智昏地接受贿赂,请人占卜凶吉。
前些事使他到处树敌,后些事使他授人以柄,于是弹劾状纷纷飞到玄宗的案上。
张说陷入了四面楚歌、孤立无援的困境,兄长张光割耳为他鸣冤也无人理会,威风凛凛的宰相终于沦为蓬头垢面的狱中囚。
幸得高力士出于同情向玄宗求情,他才免于身首异处。
东山再起的结局,是休致回家写作历史。
在处理张说的问题上,玄宗心里是矛盾的。他希望有个精明强干的宰相为他挑起重任,但又不愿皇权遭到削弱。这是个永远无法妥善处理的难题。他权衡再三,为了皇权的集中还是牺牲了张说。
当然,张说不是没有过错,他受贿,宰相受贿对政府名声不好。为改善政府的形象,玄宗特地挑选了以清廉俭朴闻名的李元纮为相。继而出于军事因素的考虑,又把高级将领杜暹召进了中枢。
源乾曜加上左右手李元纮、杜暹,形成三驾马车。
3、正直大臣搭班子的麻烦对这驾马车的配备,玄宗不无道理。源乾曜为人宽和,可起协调作用;李元纮熟悉民政,能主持常务工作;杜暹长期驻边,善于处理中外及民族关系。
李元纮不是无名之辈,多年在宦海的所作所为使他成了一个响当当的正面人物。他有骨气,有正气,当年太平公主与寺庙争夺碾硙(利用水力灌溉及加工粮食的装置),他负责断解,实事求是地判决公主败诉,面对公主党徒恫吓,大义凛然地说:“南山可移,此判难改!”
在一步一个台阶升迁的经历中,他多次受到民众的喝彩。
为官正直是他的坚定信念,上任后,他对不学无术及钻营门路求仕者,都毫不犹豫地回绝,使官员素质有了某些改善。在少数人的谩骂中,他赢得了更多人的崇敬。
在经济上,他反对盲目的变动,主张尊重传统的合理性。
杜暹也不是无能之徒,他的儒将风度在大西北享有盛名,武功是平定于阗(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一带)叛乱,文绩是安抚将士,和治各族关系。他也相信做人应清正勤俭,青年时曾发誓绝不受亲友馈赠。
按理说,李、杜二人秉性接近,且文武之道,各有千秋,当能一唱一和,相辅相成,然而合作的事实却是大相径庭,闹成了僵局。
错就错在秉性相近,他们都算得上是刚直之人,但刚直得谁也不肯谦让,都想当主角,不愿当配角,难以达到互补效应。他们急躁无度量,为公负责变成了争死面子。大家意气用事,失了和气。
实际上他俩谁也不是当主角的材料,被选为主角的源乾曜也非当主角的材料。主角不像主角,不是主角却要争唱主角,戏怎么唱得下去?
中枢乱了阵脚,无法工作。源乾曜明哲保身,遇事模棱两可。李、杜对所有问题总是各执一词,难以一致。
玄宗又气又恼,他对三驾马车迅速失去信心,三驾马车不耐久力,驾车人玄宗想再换一辆试试。
4、“龙武功臣集团”的覆灭当初扶助李隆基走上政治巅峰的功臣,可分为两种力量,一种是以刘幽求为首的政治势力,一种是以王毛仲为代表的军方势力。
两种势力的合流,造成了李隆基的成功。李隆基成功后,为了下一个的成功,除去了政治势力而保存了军方势力。
李隆基保存军方势力,不是出于善心,而是避免大逐功臣的恶名,更重要的是保持军队的效忠和稳定。
这些军界要人,主要供职于李隆基所控制的禁军——龙武军,故被史家称为“龙武功臣集团”。
掌握政权,需先掌握军队,掌握军队,少不了代理人。对君主来说,代理人应是驯服的狼狗,对外当示以利齿锋爪,对他则要绝对的温顺听话。龙武功臣集团不太懂这个道理,他们错误地以为自己有功,对似乎离不开他们支持的玄宗缺乏诚恐诚惶的恭敬,还敢自以为是地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要求。
作为龙武功臣集团的核心人物,王毛仲确实非同寻常,有着让人一见倾心的魅力,及由此而产生的高度组织力。在李隆基尚人微言轻的时候,他就凭着豪爽洒脱且机智灵巧的风格,将一批禁军军官,即后来的合作者,拉进了李隆基集团,从而控制了武装力量。此功不谓不大,李隆基视他不谓不重。
他虽肯为李隆基建大功,却不肯出死力,他看出李隆基会成大气候,关键时又怀疑自己的眼光;他敢下大赌注,而不敢一宝押到底。他是个骨干,是个不坚定的骨干,在诛韦战役的前夜,借故避开了。
玄宗爱他的才干,却不太欣赏他的品行,故而在大封功臣的时候对他虽不吝高爵美勋,但没有让他进入核心领导图。
王毛仲对这些封赏不感兴趣,他的目标是兵部尚书,由此一直耿耿于怀,认为君主恩典有限。尽管如此,他还是完成了份内的工作,并且完成得很出色。他在军队中的职务是直线下降,成信却以老资格和公正刚直而直线上升,大家信他、服他、听他。
他豪放而不乏细腻,在当“弼马温”时,把马政管理得有声有色,使马的数量迅速上升为历来之最。他还艺术地将马按色分群,远远望去,如几大团彩云在绿毯上翻腾,壮观得很。他因此被授以最高荣衔——开府仪同三司。
他在龙武军中盘根错节,和负责人葛福顺不仅旧谊笃深,还是儿女亲家,其他军官对他也多表示出由衷的钦服,公推为带头人。在他的凝聚下,龙武军官们紧密地抱成一团。
王毛仲因清高而产生的傲慢,和当时还不起眼的宦官结成了冤家,他看不起宦官,除了冷漠,就是凌辱。这使大大小小的宦官对他都窝着火,恨之入骨。
把禁军拧成一股绳,让君主不舒服。和宦官结冤,使内廷对他伏下了杀机。王毛仲缺乏对官场机制的了解,带着他的兄弟们一步步走上绝途。
在王毛仲添丁之际,高力士奉旨前去祝贺,授新生儿为五品官。高力士回来汇报,王毛仲说:“此儿难道不能做三品官!”玄宗勃然大怒,出口骂道:“昔日诛韦氏时,此贼心持两端,朕未与计较。今竟敢借婴儿怨朕!”高力士乘机进言说:“禁军豪奴,官职太盛,若不除掉,必有后患。”
玄宗未作回答,心中有了主张。
待到太原官员上奏王毛仲向他们索讨军器时,玄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发出了特别诏令,将龙武功臣王毛仲、葛福顺、卢龙子、唐地文、李守德、王景耀、高广济及王毛仲之子王守贞、王守廉、王守庆、王守道,尽数贬到边远地区。随后又发出追加令,赐王毛仲自裁。
龙武功臣集团彻底覆灭专业配资网站,玄宗去掉了最后的心病。近20年的政治经营,玄宗让所有人都懂得,不管你过去是什么身份,对天子绝对不能讨价还价。
发布于:山东省佳禾资本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